当前位置: 首页> 中心新闻
中心新闻
CCAP 30周年回忆录系列 | 王红林:回忆在CCAP的青葱岁月
发布日期:2025/09/11 来源: CCAP
作者:王红林 农银国际董事总经理、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2000年毕业生
此时此刻,坐在从上海开往香港的高铁列车上,看着眼前的景物像放电影一样向后飞驰,我的思绪回到了在CCAP的青葱岁月。二十多年了,有些记忆开始模糊了,可是在CCAP的点点滴滴却终身难忘。因为在CCAP的三年, 是我人生最重要的转折,在这里,我不仅结识了尊敬的师长和同学们,完成了硕士学业,更收获了我的终身伴侣(我的太太向青,也是同届CCAP的学生)。可以说,没有CCAP,就没有我今天幸福的人生。

人生是很奇妙的, 年轻时一个看似不经意的选择,却决定了后面的人生道路。我仍然清晰地记得,那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我第一次来CCAP, 见到我的导师张林秀博士的情景。那是1996年的秋天,我当时正在农科院对面的人民大学学习,因为很近,我就骑了个自行车来了农经所。我当时完全没意识到,这短暂的几十分钟将会彻底改变我的一生。
说实话,我当时还不知道CCAP的存在,我手里拿到的, 只是农科院研究生院的一个招生简章,上面好像只有专业名称、导师和招生人数这些简单信息。我当时对农经专业也知之甚少,我也不知道应该报考哪位老师。可能是天意,我和CCAP就是这么有缘,我一进农经所那古朴的大楼,在楼梯上问一位工作人员:招生简章中哪位老师今天在?那位和蔼的女士说:我刚才还看到张林秀老师在,你去找她吧。
我按照她手指的方向,轻轻推开了CCAP的大门(也推开了我人生幸福的大门)。当时CCAP在中国农科院农经所大楼二层的两三间办公室里,人员很少,好像就五个人(黄季焜老师,张林秀老师,乔方彬师兄,喻闻师兄,和秘书黄佳林)。我说明来意,秘书把我引到张老师的办公室。张老师当时正在忙,对于我的突然造访,完全没有准备。可能张老师也是第一次招研究生,也不知道该对我说啥,只是问了我一些简单的情况。不过短暂的交谈之后,张老师渊博的学识与和蔼亲切的笑容,让我下定决心,我一定要考上张老师的研究生!
几个月后,经过艰苦的拼搏和一些曲折,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农科院的研究生。我这辈子经过了那么多场考试,包括在美国读两个博士的多次考试,可是最难的考试,我觉得就是当时中国的研究生入学考试。那个年代的研究生非常少,当时整个农经所一年招研究生的数量不招过10个,考试实际上是非常难的。
在农科院上研究生,和大学里不一样,有点像半工半读。我们一面在研究生院上课,一面在所里工作。那个时候的研究生人数少,加上之前计划经济时代,研究生本来就是一个正式的工作,所以那时候研究生跟工作人员差不多,所里也没把我们当外人。我记得,一开始的时候,乔、喻两位师兄就像两个大管家,除了日常的研究工作之外,什么活都干。后来小林姐来了之后,情况才变得正规起来。
在CCAP读研究生, 和农经所的其他科室相比,有三个最大的特点是:年轻、国外合作多和农村调查多。首先、黄老师和张老师那时候都刚刚从国外回来,都很年轻,当时才30多一点。几个研究生和秘书也都是年轻人,所以那时候的CCAP像一个年轻的大家庭, 黄老师和张老师就是两位年轻的家长, 带着一帮年轻人共同学习与做项目,虽然很紧张,有时甚至很艰苦,但那是一段青春洋溢的时光,那是一个活力四射的年代。
我记得有一年农科院举办一个文艺汇演,当时黄老师和张老师花巨资给我们每个人都买了一套上好的演出服装,那是我第一次穿上有品牌的西服和衬衫,第一次系领带。我还清楚地记得,黄老师的爱人王琴芳老师,给每个人上台整理服装的情景。那是我第一次系领带,在正式场合登台演出。之前我从来不知道领带和衬衣有颜色搭配的问题,我记得当时王老师教我们挑领带颜色的学问:“青加紫,不如死”。这让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衣服颜色的搭配是有大学问的。
除了紧张的学习工作之外,CCAP那时候业余生活也是很丰富的。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几个年轻人经常到楼下打羽毛球,苦于没有羽毛球网。那时候可没有像现在这么方便的淘宝和网上各种体育用品(那时候根本就没有手机,电商和微信!)。没有羽毛球的网,找一根绳子拉上就可以,但是比较难办的是,要找两个杆子,底座要足够重,才能拉得住这个绳子。我灵机一动,找了两根金属棍,买了两瓶酒,到附近的工地,找正在搅拌水泥的工人帮忙,给我做了两个水泥墩子,把那两个金属棍浇铸在中间。这样,一个简易的羽毛球网就做成了。我们有了这个网,几个年轻人经常在楼下打羽毛球,打完球后,老马(马恒运老师)经常请我们下馆子,好不惬意。
那时候CCAP另一大的特点就是国际交往多。最突出的就是斯坦福大学的Scott Rozelle(罗斯高)教授。那时候Scott很年轻,应该不到50。他那时候常年待在CCAP, 和黄老师张老师密切合作,也经常带着我们下乡做调查,他就像是CCAP的第三位家长一样,和我们每个人都很熟。那时候也经常有其他国家的老师来访问。例如现在ADB当首席经济学家的Albert Park, IFPRI的樊胜根,多伦多大学的Loren Brandt等,这些老师的到来,不仅让我们开拓了视野,更让我们这些年轻人,接触到了世界农经学界第一流的研究与学者。
在这些国际知名学者当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日本教授。IFPRI的Junichi ITO(伊藤顺一)教授。伊藤教授来中国访问,需要到中国的农村去实地考察,那时候所里没有人陪,就让我陪着他去江苏调查。说实话,那时候我的英语不好,估计连现在的高中生都不如。我一路上只好连比划,带蹦词地跟他交流。他的英语比我好很多,但是英语也不是他的母语,所以沟通起来还是比较困难的。好在我们俩一见如故,脾气很合得来,所以很快就成了朋友。我记得当时我们在无锡调查的时候,在一个小饭馆吃饭,他指着旁边的女服务员跟我讲,15年后,这个服务员就有钱去日本旅游,当时我是真的不信,因为那大概是1998年,我还看不到日后中国的快速发展,而这些国际大学者已经看到了。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2000年左右,我记得Scott鼓励我们每个人在北京买房,越多越好,可惜当时我也没听懂,CCAP有些老师就听懂了,说明老师确实比学生目光远大,也可见当时这些国际大学者,对中国的判断是正确的。关于伊藤教授,还有一件小事,在南京调查完之后,我顺便带他参观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参观的时候,他那震惊和害怕的表情,我印象很深,可见当时在日本国内,很少有人知道曾经发生过这么惨烈的大屠杀。从那以后,他每次来中国,都会请我吃饭。
那时候我们去农村调查很多,我记得第一次跟张老师一起出差去农村调查,是去朱德元帅的老家四川仪陇县。那个地方当时是真苦。我记得当地农村的妇女要挑土上山,把土放在山上,就为了种一两棵玉米,那个工作强度太大了,也让我理解为什么四川的女人那么能吃苦。我们参观当地的小学,看见一群孩子在一个黑洞洞的屋里读书,没有电灯,就靠一个小窗照过来的自然光,那个场景,让我终身难忘。我们从仪陇县调查回来的时候,满腿泥浆,身上都是土。返回成都住宾馆的时候,宾馆保安那鄙夷的样子,也让我们很难忘,当时雷明国就跟我说,他不是觉得我们没有钱吗?等我们有钱了,用钱把他们砸趴下。
农村调查是很苦的,调查问卷往往很长,到村里访问一个农户,一般需要两到三个小时。我们的调查问卷如此详细,往往一个农民在回答我们问题的时候,他老婆会说,这个事我怎么都不知道! 我们做农户调查,最考验人的耐心,经常问到最后,被访问的农户已经一副你饶了我的表情,但是我们都要仔细认真记录好每一个问题(那时候,大部分农户没有手机,电话回访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一天要访问好几个农户,时间非常紧,往往都来不及吃饭。农村调查很苦,但是也有很多乐趣,特别是能吃到很多当地的美食。
现在回想起来,我这一辈子吃的最美味的两顿饭, 都是在CCAP做农村调查时候吃的。我记得有一次在陕西安塞县做农户调查,调查结束后,县里的同志安排我们在县招待所吃羊肉和馒头。那个地方的羊,当地人说是吃甘草长大的,一点都不膻,确实非常美味,那个地方的馒头也是自然的纯手工做的,非常香,我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馒头。热腾腾刚出锅的馒头加上羊肉,满满一盆,加上调查后的饥肠辘辘,我一连吃了5-6个馒头,真的是一绝,让我现在想起来都直流口水。
还有一次是在安徽金寨,好像是冬天,在山里调查,深一脚浅一脚,在山里走了大半天,终于完成了当天的调查任务。晚上天黑了回到当地的一个镇上,乡里的干部请我们吃当地的烤腊肉。那红红的小铁炉端上来的时候,不仅驱散了我们身上的寒冷,那一口鲜美的土腊肉,真的是太好吃了,我再也没吃过那么好吃的腊肉了!
调查的生活不仅可以尝到美食,而且可以增长很多见识。我记得有一次去宁夏同心县去调查,那是一个少数民族地区。当地的林业局长是一名回族的干部,调查完了之后,他邀请我们一起去卡拉OK,喝完酒后,他即兴引吭高歌,我印象很深,那首歌好像是关于雄鹰的。高手在民间呀,他那个水平,我觉得跟刀郎差不多。可惜那时候没有微信,如果有微信的话,我和他就可以保持联系了(微信这十几年,真的改变太多中国人的生活了!)。
CCAP的三年生活,紧张、充实、艰苦并且快乐!CCAP的各位老师们,不仅教授了我们专业的学识,更是在我们的事业与生活方面,真正起到了导师的作用!我永远感激CCAP这个温暖的大家庭, 感谢各位老师和同学们,让我和向青度过了最难忘、最精彩的青春岁月。我们一家人都十分期待下个月,CCAP大家庭的三十周年Reun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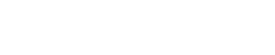


 本站首页
本站首页




